十九岁的生日,我在学校默默无闻,不知道谁给我祝福。
深夜十二点的时候,电话***响起,是母亲打来的,母亲沙哑的声音从遥远的家乡传过来:
今天是你的生日,过得好不好?
我说我很好,很开心,很多人祝我生日快乐!母亲在那边笑了。
那就好,妈不在你身边,要好好注意身体。
我说,没事儿,妈,我能吃,能睡。好得一塌糊涂。还在这边夸张地大笑。
母亲终于放心地挂了电话,我却想哭。
离开家那么久,从来没有一次会因为想家而哭泣,觉得哭了也没用,人还是在这里,家还是在远方,很少打电话,害怕。母亲沙哑的声音总是让我有揪心的感觉。况且说来说去,总是那么几句老掉牙的话。也很少写信回家,我的字通常都是龙飞凤舞,母亲说她老了,眼花,不认得。我笑她说,认字不多直接说好了,说眼花,笑死人。
偶尔,我会想起小时候,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放学了就和邻居家的伙伴一起爬树、翻墙、抓龙虾,还特别喜欢打架,母亲拿我没有办法,常常挥舞着翠绿翠绿的竹条追着我打。我会扭过头看看她,做个鬼脸继续跑,她在后面追着大喊叫我别跑,再跑就打断我的腿,我则是更加拼命地往前冲。
母亲变得温柔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十六、七了,处在一个开始懂事,开始思考的年龄。我常想是不是因为一直以来我的倔强和任性,母亲的忙碌与***,以致于数年后我们不在矮有冲突和争吵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经将我们变得陌生,母亲已经不再如当年那样矫健,皱纹多了,笑容少了,皮肤黑了,头发白了。有时候,我思考母亲的人生,多过于思考自己的未来。我知道,这么多年她第都在极力回避和阻止许多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的事情。在我小的时候,在她老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在尽我们所能去追求一种美好的生活,追求一种我们想要的生活,尽管很辛苦,我们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执着。
当我在这里,母亲在那里,我们有了各自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我发现不知从合适起,我会特别地怀念那个母亲追着我打的年代,无忧无虑,天真无邪。那时世界是一幅美丽而简单的画,画上小桥流水人家。如今我站在这里,想着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于是,我知道,我是爱母亲的,我爱她一如她也同样地爱着我,是是我爱她,我说不出口, 她爱我,却也拙于用言语表达。
那个深夜十二点的电话,让我在那一夜辗转难以入眠,我以为我而可以写些什么给母亲,以纪念她这些年来不管有意或是无意中教给我的生活理念。却发现,无论何时,言语似乎都是多余。我们对于彼此的爱,已不再需要一字一句,却已经在岁月中深深蕴藏。
深夜十二点的时候,电话***响起,是母亲打来的,母亲沙哑的声音从遥远的家乡传过来:
今天是你的生日,过得好不好?
我说我很好,很开心,很多人祝我生日快乐!母亲在那边笑了。
那就好,妈不在你身边,要好好注意身体。
我说,没事儿,妈,我能吃,能睡。好得一塌糊涂。还在这边夸张地大笑。
母亲终于放心地挂了电话,我却想哭。
离开家那么久,从来没有一次会因为想家而哭泣,觉得哭了也没用,人还是在这里,家还是在远方,很少打电话,害怕。母亲沙哑的声音总是让我有揪心的感觉。况且说来说去,总是那么几句老掉牙的话。也很少写信回家,我的字通常都是龙飞凤舞,母亲说她老了,眼花,不认得。我笑她说,认字不多直接说好了,说眼花,笑死人。
偶尔,我会想起小时候,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放学了就和邻居家的伙伴一起爬树、翻墙、抓龙虾,还特别喜欢打架,母亲拿我没有办法,常常挥舞着翠绿翠绿的竹条追着我打。我会扭过头看看她,做个鬼脸继续跑,她在后面追着大喊叫我别跑,再跑就打断我的腿,我则是更加拼命地往前冲。
母亲变得温柔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十六、七了,处在一个开始懂事,开始思考的年龄。我常想是不是因为一直以来我的倔强和任性,母亲的忙碌与***,以致于数年后我们不在矮有冲突和争吵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经将我们变得陌生,母亲已经不再如当年那样矫健,皱纹多了,笑容少了,皮肤黑了,头发白了。有时候,我思考母亲的人生,多过于思考自己的未来。我知道,这么多年她第都在极力回避和阻止许多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的事情。在我小的时候,在她老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在尽我们所能去追求一种美好的生活,追求一种我们想要的生活,尽管很辛苦,我们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执着。
当我在这里,母亲在那里,我们有了各自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我发现不知从合适起,我会特别地怀念那个母亲追着我打的年代,无忧无虑,天真无邪。那时世界是一幅美丽而简单的画,画上小桥流水人家。如今我站在这里,想着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于是,我知道,我是爱母亲的,我爱她一如她也同样地爱着我,是是我爱她,我说不出口, 她爱我,却也拙于用言语表达。
那个深夜十二点的电话,让我在那一夜辗转难以入眠,我以为我而可以写些什么给母亲,以纪念她这些年来不管有意或是无意中教给我的生活理念。却发现,无论何时,言语似乎都是多余。我们对于彼此的爱,已不再需要一字一句,却已经在岁月中深深蕴藏。

[本帖已被作者于2005年8月17日22时40分29秒编辑过]
请登录后发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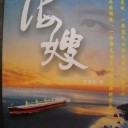
 联系我们人工客服
联系我们人工客服



















 :1391995811
:1391995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