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沉闷的夏天,嘈杂的都市,匆忙的人流,人们除了自己,似乎已经忘记了还有什么,我也是。
这个夏天的某一天,我带着自己回到了那曾属于我的地方——岛,我的家乡,一座与大陆一水相隔的小岛,船是这里唯一可以与外界相通的工具。
回家的第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散步于沙滩,突然起了大风,海上卷起了巨浪,冲着我铺天而来,我拼命地逃,可最终也还是没入狂涛骇浪中。我惊醒过来,喘着气,回想刚才的情景仍心有余悸。定了定神,外面已是鱼肚白,还是去海边透透气,看看久违的日出吧。
天已蒙蒙亮,路上除了早起的农夫和他们心爱的老牛,却只有我……对,还有咸咸的海风。清晨的海很恬静,像个温柔的母亲抚摸着沉睡的沙滩。远远的海天之间罩者一层薄薄的雾,像是从海上升腾而起,又像是从空中倾泻直下。我沿着沙滩走着,海浪轻抚我的脚,海风吹拂我的脸,一股清凉到心的感觉。天慢慢地变蓝了,雾也渐渐地褪去,远处的小屿凸现了出来,海面上有水鸟在盘旋,沙滩上有沙蟹在嬉闹。偌大的一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拣了块地方坐了下来,独享这大自然的恩赐。
正当我陶醉于以为是自己的世界时,身后响起了“沙沙”的脚步声,缓缓地、轻轻地。我回头去看,是一个少女,一身朴素的白,正踱着轻轻的步子向我走来,一头披肩的长发随风舞动,要不是她那张忧郁的脸,那双忧郁的眼睛,我真的会以为她是天使。
此刻她也看着我。我终于看清了那双眼睛,目光充满了感伤,那里面肯定藏着痛苦的回忆,我不忍多看。
“你是来等船的吗?”她先开口了,声音有些凄凉,并且在船字上加了明显的重音。
“不,我是来——来看日出的。”不知为什么,我讲得很小心,怕触动了她。
“看日出?你家不是打渔的吗?”
“不是。”我竟然觉得有点遗憾,连忙弥补,“不过,我有许多亲戚、朋友都是打渔的。”
“那你觉得打渔怎么样呢?”声音依然是慢慢地。
“打渔。好啊!驾着船出海,与世无争,自由自在,多好啊!”我也被自己陶醉了。
“嗯?你好象不是这里的人。”我刚想说明,她指一指远方,“看,太阳出来了。”
我转过身去看,海的那一边冒出了一个红通通的东西,洒下一片金光,顺着海面窜到了我身上来,大海笑了,沙滩醒了,海鸟欢快地叫着,一时间我觉得这些如此陌生,我不是这里的人吗?
不远处的海港,已有船扬帆出海了。
“你看到那些船了吗?”我点头。
“你知道它们何时能回来吗?”声音变得悲伤。
“也许——可能,呃……也许几天后就能回来吧?”我不知所措。
“嗯。也许几天之后就回来了。但也许,也许再也回不来了。”声音深沉,她像是在回想什么。
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我努力地寻找着词语,可此时却是一片空白。
她说她要走了,我目送着她远去。
“嘿!今天天气这么好,应该没事。”我突然叫了起来,发自内心的。
她回头报以一个微笑,那一刻我真地以为她是天使。
海面上,船多了,向着海平线,向着太阳奔去。不知它们带着什么而去,也不知它们带着什么回来。一种莫名的感伤袭上心头。
又是一个晚上,小武来找我。小武是我儿时的好友,后来虽各自走的路不同,但彼此间的友情未变。小学毕业时,他就退了学跟着他爸出海打渔,那时候起我就对他羡慕不已,时常在家里的饭桌上埋怨说,我们家为什么不是打渔的;我考上大学那年,他有了自己的船,成了船长,我对他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恨自己报的为什么不是航海学院。
起初,他给我讲海上的趣闻;讲晨曦乍现的黎明、繁星满天的夜晚;讲见所未见的鱼、闻所未闻的礁;讲怎么看天气、方向、流水……他讲得津津有味,有一股船长的自豪。
后来,我们喝了酒,他开始变得激动了。
“你相信有神吗?”他突然问我。
“啊?”我一楞,没想到他会问这个,“你是指关公吗?”这里有个风俗,打渔的人拜关公,所有的船都到庙里请尊关公坐镇,保佑全船平安,“这只是风俗嘛,打渔在外,找个精神依托也是应该的。”我不知如何回答,就随便扯。
“不,我信。我亲眼见过。”他眼睛盯着酒杯,像是陷入了沉思。
“那——那也许是你的幻觉吧!”我举起酒杯,“来来来,不谈这个,喝酒。”
“不!”他依然盯着酒杯,“实实在在的。那次出海,我正在甲板上张罗着伙计们放网,发觉船头上站着个人,一看不对劲,以为自己看花眼了,咱毕竟也读过几年书,不太信那个。可仔细再瞧,他仍立在那里,而且好象在跟我讲,快回去吧,有危险。当时心里头有点虚,于是下了狠心,叫伙计们收网回来了。”
“结果呢?”我已忘记自己不信那个。
“结果?”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又斟满,“结果我们回来了,第二天就起大风,有船没回来。听说明天晚上就引魂了。是啊——都一个月过去了,没希望了。来,喝。”他又干了一杯。
再后来,他喝醉了,又叫又唱地,似乎也哭了。我也想哭,不知是为他还是为我自己。
引魂,也是这里的一种风俗。人死在外边,就举行这种仪式把游魂招回来;出海的人死在海上,一般都是夜晚在海边进行这种仪式。
第二天晚上,我去了海边。没有月亮,只有满天的星星;沙滩上人很少,只有海浪“刷刷”地在低吟;海黑黝黝的一大片,只有远处灯塔的光每隔一段时间后又会从身旁划过。夜很静,海也很静,海风徐徐而来,像情人的细语,让人只感到海的宽容而并非它的暴戾。
引魂的人们来了,远远的就听到女人的哭声,哭声凄惨,像是在申诉,但又饱含无奈,也许她不知该向谁申诉。风有点大了,呼呼地作响。引魂的人们近了,我看到了那个***,被人扶着走,扶她的人也不时地抹着眼角。女人的后面紧跟着就是一个小女孩,别人牵着,也许她意识到她会失去什么,那只纤小的手紧紧地拽住牵她的人的手——此时她唯一的依托;也许她发现人群中少了什么,那双惊惶无助的小眼睛四处张望着,像是在寻找什么;小女孩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我看清了那含着泪花的眼睛,它像对我说,我害怕,我害怕!她哪里知道以后当她问,爸爸去哪里啦?她将听到是,***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此刻,我心头一震,那感觉让我想起那个清晨那位少女的目光。风又大了,海浪“啪啪”地叫着。
“嗨,又是你。”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果然是那位少女,不知何时她已来到我的身边。
“哦,来看引魂的。我从没想到打渔会这样。”
“唉。本来就是这样的。有谁知道老天爷在想什么,哪一天他不高兴了,就有人回不来了。”她像是在控诉。
“我一直以为打渔、驾船出海是多么美好。”我苦笑。
“美好?怎么可能呢。男人们为了养家出海,除了盼望每次出海会有收获之外,还得提着一颗心希望自己能平安回去。”她别过脸去看海,“而女人们也得揪着一颗心等着,天天跑到渔港去看丈夫的船回来了没有。”
“那你呢?你是来等船吧?”我想起上次的谈话。
“他们都说,别等了,不会回来了。”她过了好久才开口,声音抽泣了起来
“可是——我不信,因为出海前,他说,这次回来就娶我。”
我无语。
后来,天下起雨来。
暴风雨过后的清晨,我独自一人到海边。暴风雨肆虐过的天空一贫如洗,太阳老早就出来了,用慈悲的目光审视着这个它消失几天之后的世界,依然如旧,它笑了,于是海鸟又开始盘旋,沙蟹又开始嬉闹,海也还是那么静,风也轻轻地吹着,而不远处的海港又有船扬帆出海了。[move] 重发此文以祭每年遇难之渔民[/move]
请登录后发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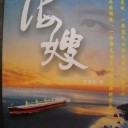
 联系我们人工客服
联系我们人工客服



















 :1391995811
:1391995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