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向往在09年5月23号那天开始实现了,整整花了三天的时间,我到了巴哈马的干船坞,很新鲜的空气,透彻的天空,干船坞离机场比较的远,代理把我送到门口,拿出张纸让我签了字就驾车驶去,还是一个人,从离开家一直到现在都是我一个人。
22号到洛杉矶时在机场里买了张电话卡,说明书就好十几页,英语,西班牙语,韩语,日语,就没见一个中国字,在公用电话机附近徘徊良久,拨了好几次电话就是打不通,拦住好几个过往的***,得到的答案居然是不会用电话卡,好不容易见一黄种人,而且很确信他就是中国人,上前寻求帮助,他居然听不懂普通话,我很诧异的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回答得很干脆,我爷爷是中国人,这也难怪,过了两代,换的不仅仅是国籍呀。得知我离开家三天都没给家人任何消息,他很同情的问我家里的电话号码,然后很麻利的在自己的手机上打出一连串的数字,但就是接不通,看了他递给我的手机,我解释说自己刚下飞机,来自于中国。听到这话,那人赶紧收回手机开始和我研究电话卡,那人也是刚下飞机,跟来机场接他的同伴商量了几句,看了会说明书,摆弄了下墙边的电话机,然后很抱歉的把电话卡递给我。
很礼貌的谢过他们后我逐字逐句的依照说明书把电话拨了出去,见好长时间没反应,我放回话筒,安慰自己说这电话坏了,换个地方可能就打通了,经过一番折腾,换过好几个电话,我才想明白,原来电话没有坏,是我的脑子不好使了,长这么大,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惊喜交加,还要在这里等六个小时的飞机,除托运的行李外,随身的手提包里就一袋泡面,与其在机场里买吃的,还不如买张卡给家里打个电话,离开爸妈那么远,他们肯定会很担心的。鬼使神差的,我不停的拨号码,一次偶然的机会,居然打通了,爸爸还在开车,接到我电话时他简单的问了我一下情况就责怪我不该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因为国际长途很贵,他没有说错,10美元就只能打五分钟。
从洛杉矶到迈阿密又是4个半小时,我依然呆在机场里,不敢乱跑,万一弄丢了会很麻烦的,21号离开家那天,妈妈哭了,说要送我到汉口,理由是帮我提行李,在学校的时候她每个星期都会给我打好几个电话,这一走,她知道很难再听到儿子的声音了。我说不用了,离开家的这半年我会经常给家打电话的。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往面盒里倒进从咖啡店里要来的开水,一股香气扑鼻而来,不管在火车上还是在北京的旅社里,我吃的只有方便面,现在闻着这香味,胃里开始翻腾,我嘲弄自己说,最后一顿中国饭啦。掰开筷子,夹起面条,猛的一吸,刚嚼一下,一群目光就聚到我的身上,我感到很诧异,不就是吃个面嘛,不至于这么羡慕吧!后来在船上也吃过几回菲律宾大厨做的意大利面,餐厅里的船员吃面都不用吸的,什么东西嚼在嘴里,声音都很小。吃面的姿态跟旧版西游记里孙悟空在面馆里的姿态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孙悟空拿的是筷子,他们拿的是刀和叉。
刚在巴哈马下飞机的时候,走进海关大厅就见一个当地人以弹电子琴向来访的游客表示欢迎,虽然听不懂谈的是什么乐曲,却感觉比较的亲切,很快的,我来到了移民局官员检查排队的地方。一个很胖的黑女人见我戴着面罩,揉着肚子,快步走到我的跟前,问道:“你不舒服吗?”我很感动地看着她,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黑女人又问了一句,我顿了顿,谢过后说没事!其实是肚子比较饿,但我没有跟她说。在北京到洛杉矶的飞机上,我一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就睡着了,错过了旅途中唯一的正餐,回答黑女人的问话时我还在后悔!黑女人没让我排队,直接让我跟着她。进了他们工作的办公室,他让我掏出护照。我很快把预先准备好的护照放到黑女人面前的桌子上。她拿起那个枣红色的本子,看看上面的照片,然后扫了我两眼,很熟练的在我的护照上盖上了移民局的专用章。我心里美滋滋的,终于碰到热心肠的好人了。
把护照递给我后她又问了我一句是不是感觉不舒服,我说没有,自己很好,谢谢她的关心。然后她莫名其妙的冒出一句:“我们这里还没有任何一列禽流感病列,如果你有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直到这时我才幌过神来,原来她怀疑我有禽流感。黑女人继续问我这几天都到过哪些地方,以及其他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我一一回答,最后又给她解释,离开家前,是父母让我戴上口罩,为的是保护自己免受感染,可她听不进去,执意要我到大厅一角的椅子上等待他们医生的到来。此时本次航班的乘客已经走得差不多了,移民局的那些官员陆续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撤下来。一部分和乘客消失在过道的尽头,一部分进了刚才我去过的那间办公室。不多会,从办公室里出来另一个光头的黑人,他走到我面前,一只手放在腰间抢的手柄上,一只手指着我身下的座椅说:“那不是你的座椅,你没看你面前的牌子上写着什么吗?”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就在我左边的桌子上放着块白色的显示牌“DOCTOR”(医生),我身体一扭,***很不自然的挪到邻近的一张椅子上。心想刚出来,人生地不熟的,得放老实点。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被领到大厅一角的小房间里,随后近来一穿白大褂的所谓医生,他让我解开衬衣的扣子,用听诊器听了下我的心跳,短短的几十秒钟里他一直跟我保留着至少半米以上的距离,体温计递给我量体温时也是面部与手臂成90˚角看都没敢看我一眼。大约15分钟后按照医生的吩咐我把体温计递到他戴手套的手上。观察半天,他才把体温计装进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之前的黑女人在小屋的出口处拦下我们,她和医生进行短暂的交流后问我随身携带了什么药品。我的回答很简单,不想再在这地方耽误时间,而她显得很不满意,领我在行李传送带附近找到了自己的行李,然后要我打开行李箱,把所有的药品翻给她看,我很顺从,可能是各项药品上标识的中文多于英文,他们瞅了半天才告诉我代理在外面等我。
依照走廊里的提示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来到机场外围的接待处,三三两两的看到一些游客,外面下着很大的雨,两个体型可以说是庞大的女人在接待的半圆形桌子旁玩着***。在我的请求下,他们给那个没见过面的代理打了电话,两人显得很热情,我疑惑的问他们为什么会知道是谁来接我,他们倒觉得有些奇怪了,因为在这里就一个代理负责船员的接送。经过漫长的等待,代理终于来了,经双方确认后我登上了他那辆可以容纳七八个人的面包车。此时雨已经停了,空气格外的清晰,路边都是一排排的叫不出名树木,偶尔可看到几处破旧的厂房。车在远离市区的海岸边停下来了,之前在飞机上俯瞰这座巴哈马最大的岛屿,心里就冒出两个字“干净”,我只能在电视上才可以看得到的海边景色,虽然没有看到布满细沙海滩,没有看到穿比基尼的美女,没有看到在冲浪板上跳舞的热血青年,仅仅就是那清澈而稍加点淡蓝色的海水,我明白自己的海员生涯就此拉开序幕。
道路由水泥变成了黄泥,车在一个大院的门口停下来了,代理帮我从车上搬下行李,随即递给我一张纸说是要签名,或许那签名是我离开家后唯一可以写下的中国字了。告别代理我在大院的门口按照值勤保安的吩咐,递给她事先准备好的护照和船东的邀请函,待检查完毕我领到一张所谓的ID,此卡是我进出这个干船坞的有效凭证,绕过几个积水坑,几排简易的工棚,我像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一艘巨大的油轮仿佛是悬在空中,当时就问自己,这是船吗?干嘛不在水里啊?船的首部就用白漆写着NORDMARK,这条船的外围用专门的护栏给圈了起来,顺着护栏我找到了登上甲板的梯子,这条超巴拿马级的油轮型深至少20米,加上比龙骨到地面的距离,约莫算来甲板到地面的垂直距离就足有25米,加之梯子与地面将近成50度角,我有些担忧了,几位好友在送我去武昌火车站的过程中把行李箱上的3个轮子拖得只剩一个,到北京后买了个新的,质量方面也不敢有多大的信赖,毕竟是便宜货。若是在上楼梯的过程中,行李箱散了架那可如何是好啊!另外,提着30多公斤的行李往上爬数百米对于一个刚走出校门的人来说似乎有些强人所难。或许就是在那时我学会了做事不能想着有人会来帮我,如果是我的工作就得自己去做,别人不会帮你,这跟团体工作又是另一码事了。好不容易登上甲板,进入视野的是整片灰色的油漆过的甲板和管路,许多白色,黄色以及红色的英文字母。我是从右舷登上甲板的,从舷梯到生活区的这段距离上我发现了供人行走的护栏,没有护栏的地方很清晰的画出两条黄色的线,两条线之间的油漆明显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油漆,上面好像有些细沙,估计是为了增加摩擦力而专门设置的。在生活区的门口处我碰到了个50多岁的伯伯,自称是水手长,看他年纪比较大就没有请他帮忙拿行李,后来发现即时要求他帮忙也只是等于白说。
水头将我领到CCR,也就是货物控制室,当时里面正坐着两人,他们似乎在商量着什么事情,见我进屋,两人起身跟我握手,经介绍才知道一个是船长一个是大副,船长关切的问道:“黄先生,你在路上的行程是多长时间?”。“三天。”我回答说。从20号晚登上火车,15个小时坐到北京,(主管并没告诉我可以买卧铺票,正如五月份到北京办美签只允许买硬座,因为只有那样才可以报销),前往机场的前半小时签了合同,都没来得及看就这样把自己给卖出去了,公司的人催我快签字,别误了班机,如果不签就上不了船,当时也没犹豫就照做了。这些都没告诉船长,心想说了也没有用。
“这么长啊!”船长显得很惊诧:“今天就没什么工作啦,你去这层甲板最旁边的那个房间住一晚上,等明天在你之前的实习生走后,你就可以搬到他的房间了,”船长顿了顿继续说:“现在去你的房间,待会把证件给我就休息去吧!”我应了一声,随同水头来到指定的房间,我拉开行李箱的拉链,拿出证件和几罐在家准备好的茶叶,顺手递给水头一罐,他显得很兴奋,接过茶叶就咧嘴笑到:“我很喜欢中国的茶,上回在美国我也买了一袋,要20美元,谢谢你啦!”实际上那茶叶是上船之前在家附近的超市里买的一大包,然后去茶叶店选了几个比较精美的茶叶罐,亲手将那大包的茶叶分装到小罐里面而得来的,反正这群老外不是很懂茶,贵的也买不起,随便送些,意思意思应该就可以啦。
道别水头,我手持所有的证件回到CCR,按照船长的吩咐将证件放到桌子上后,然后问船长现在可不可以给家里发封邮件,船长说:“待会儿”。我刚想解释说这么长时间没给家人联系,想报个平安,话刚说到一半,船长变吼道:“滚出去。”大副在一旁没敢支声。
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才有时间观察房内的布置,靠门立着个衣柜,衣柜的旁边是写字台和一把椅子,写字台上除了盏台灯和一部电话还有窜钥匙,房间的尽头有扇密闭的圆形窗户,一张单人床倚着墙角,咖啡色的毛毯铺盖着洁白的床单,我把行李箱挪到床边的沙发上,找出些必需品,因为就在这住一晚,也没必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不多久便有人敲门了,刚打开门就听到了久违的普通话,高我一届的实习生告诉我说他的那间房比这里环境好多了,至少比这间大,还有**的卫生间,不用像这样俩人供用。和他一起的那人跟我们年龄相仿,头发比较卷,听说是埃及的,******,不吃猪肉。
我从行李箱里翻出一盒烟,拆开封口递给他们,埃及三副接了根,说是想尝尝鲜。抽罢烟,旧实习生带着新实习生去泵舱甲板溜达了一圈。虽然三天没有躺在床上睡过觉,特别的困,但刚到这地方,难以压抑心中的兴奋,觉得什么都很稀奇,同时一股压力慢慢的爬上我的神经,头一次上船,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的,以前培训的时候在武昌江滩的一艘船上呆过过几次,而那船比较的小,顶多3000吨,跟现在的105000吨相差甚远,况且那条用于培训的船还是静止在江里,可移动的船我也坐过,江里的轮渡,十五分钟由江的一头到另一头,靠岸之前转向停车,还可以玩玩漂移,这条就不一样了,尽管现在在干船坞,看不到它驰骋于大洋中的壮观,可它迟早要下水的呀。
在大副的帮助下,一个住隔壁的OS,也就是二水布朗把卫生间的门打开了,那时才知道卫生间里通向两个房间的门是可以在卫生间里锁上的,这样为确保隐私,在一人使用卫生间的时候可以将通向另一个房间的门锁住就不用担心对方打扰了,洗完澡,我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次日8点水头找到我,说当天的工作是跟他们一起下机舱,具体事宜得到了才能解释清楚,我很顺从,跟着他们那伙人来到机舱的底部,那里面很热,不透气,还有股铁锈参着黄油的味道,巴哈马在赤道附近,温度常年比较高,我刚开始站着,然后蹲着,主要原因是不想弄脏身上的工作服,自己的工作也是比较明确的,刚下来不久水头就递给我夹着几张纸的文件板,让我在纸上记下他们的名字和每回进出污水井的时间,同时向驾驶台汇报,看着那几张纸,全英文的,勉强可以看懂是进入密闭空间的许可证,上面有大副和船长的签名,四个菲律宾水手自带工具下到污水井,在他们之前已经把橙红色的通风管放了下去,通风管的尽头接着鼓风机,他们下去时,顺带着一盏好像矿灯的照明装置,灯尾部的线比较的粗,后来才知道里面没有电,全是靠空气使之工作的,水手们下去后将通风管又往舱的内部拽了拽,几人分工合作,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机舱有些噪音,听起来有点心烦意乱的,没蹲多久就扛不住了,四下看看,找了块他们还没有用的碎布,铺在离污水井舱口比较近的地方坐下来,向前探探头就有那种清风拂面的感觉,风是由污水井的舱壁反弹出来的。整整一天,我做得最频繁的也就是拿着对讲机问他们在井底是否安全,然后汇报给驾驶台的值班驾驶员。临近下午,答应去送老实习生的,可惜一直走不开,宾仔们时不时出来透气,还不让我告诉驾驶台他们已经出来了,那么大热的天也可以理解呀,大约是在下午5点钟左右,他们结束工作,递给我一桶从污水井里掏出来的烂铁,说是要我提到甲板的垃圾堆扔掉,很沉的一堆铁由机舱底部到甲板将近4层楼高,到甲板时我都快喘不过气来。
吃罢晚饭,我将行李由临时的房间搬到属于实习生的那间,这地方比较宽敞,地上还有地毯,可惜已经是油迹斑斑,进门靠左手有件救生衣,浸水服在衣柜内专门的一格躺着,床是双人的,其他的布置跟之前的房间差不多,床上的床单和被套有些泛黄,听说可以找服务生更换的,房间里有两个挂钩,上面还保留着上任实习生留下的工作服,衣服上五颜六色的油漆和油渍使得原本就不怎么好看的连体衣更加的丑陋。房间里由于长时间没有清理显得特别的凌乱,于是找来服务生,手里捏着事先在电子词典里查到的关于床单,被套和枕巾的单词。
服务生费布斯比较的热情,帮我更换了床上的用具,还提供了些卫生纸和洗衣粉,但却不愿意帮我收拾房间,只是给了我一个黑色的垃圾袋,让我自己处理。谢过费布斯,我把房间里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股脑全扔垃圾袋里,其中就包括那两件工作服。
垃圾堆就是放在船中附近的一个铁型槽,回来的途中碰到二副,他直接说了句跟着我就朝旋梯走去,也不顾我听懂没听懂,二副也是埃及的,留了很长的络腮胡子,听说他每天起床要像洗头那样洗胡须,还要用梳子梳好长时间,二副没走几步便停下来回头看我,见我愣在那里便说道:“过来。”跟着二副下了旋梯,拐过几个弯就到了船坞的门岗,六点钟的巴哈马似乎没有天黑的迹象,路边的水坑里,雨水泛着黄色,下班的人群依旧陆陆续续的离开,二副和门卫进行几句简单的交涉,从门卫亭里端出两个纸箱递给我,签完字,他手一挥,示意我跟着他,丝毫没有接回纸箱的意思。旋梯依旧很高,二副走到半途就倚着护栏休息,可能是新上船,身上有着使不完的劲儿,我三步并作两步在距二副约8米远的地方等着他,几分钟后二副喘着气在我之前上了甲板,他要求我将纸箱送到驾驶台,然后去他房间找他。
二副的房间在B甲板,敲开房门,我很主动的脱掉鞋,在他的示意下坐到沙发的一角,他随便问了些我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在船上的适应情况,我一一回答,末了,他说跟菲律宾人要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又不能走得太近,至少得保持一定的界限,他的语气比较的平缓,发音也很标准,但是说到“boundary”(边界)这个词时见我有些疑惑,他便走到一旁,指着墙上的地图说,这就是边界的意思,我也起身,顺着他手指的那条线,似有所思。谢过二副,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越想越不理解,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不是越融洽就越好吗,干嘛非要隔着一层啊?
看看表,还只八点,比较的早,于是打开门想到外面溜达溜达,多熟悉熟悉环境,看看应变部署表,先弄明白在各种应急情况下我的职责是什么,途径货控室时,见三副阿雅德和二水布朗·柯斯在里面坐着聊天,我便走了进去。见我的加入,他们都表示欢迎,三副递给我一支万宝路的香烟,当时有点紧张,不敢在货控室里抽烟,三副宽慰道:“不要怕,这里抽烟没人会说你的,船长现在不会下来的。”点着烟,我好奇的问:“咱们的船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呀?”我的发音在他们看来还是不很容易接受,他们看上去也不像是听懂了,于是我重复了一遍,三副回答道:“一个月前我们的船搁浅了。”他好像说了个我不知道的地名,但具体是哪里,也不大懂,当时表示出一副惊颤的表情:“搁浅?怎么可能呀?”“是的,我们确实搁浅了。”二水布朗肯定道。
“那你们可以给我讲讲事情的经过吗?”这回我把语速放得很慢,中式英语估计很难让人理解。
“当然可以,想必你也见过现在的船长了,”三副的表情显得有些沮丧:“他比你早到两个星期左右吧,之前是个印度的船长,30 多岁,人很不错的,就是因为船搁浅的事,公司才会派遣现任船长取代他。”
“那以前的船长呢?”我惋惜道。
“ 应该是被开除了,不然现在也不会跟这个该死的船长待一块了。”二水布朗补充说。
写的不错,继续努力。
操作:平凡人
[/bonus][bonus]经验值 +10;虚拟货币 +100;人气值 +22欢迎原创作品
操作:oasis
[/bonus]请登录后发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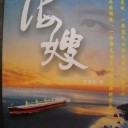
 联系我们人工客服
联系我们人工客服



















 :1391995811
:1391995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