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从海运学院毕业后,11月初公司就派我到秦皇岛上“明海”轮干实习水手。
“明海”轮是一艘南斯拉夫1964年造的载重吨36000吨的散装货船。长198米,宽32米,吃水10米,7个大舱,5组10吨的船舶吊。12000匹马力的内燃机,节能航速13节。船上52名船员。
按国际海协的规定:船龄在10年以内为新船,10-18年的为旧船,18年以上为老船,老船在有些国家就不给注册了。也就是说不准航行了。可我们国家那会穷呀,只能买这些人家淘汰下来的旧船用来跑远洋,当我登上这条又旧又老的船时,唯一可以让人有点信心的是南斯拉夫人造的船钢板用的厚,十几年了,看上去船还很结实。
船当时停在秦皇岛锚地,她刚从美国拉小麦回来。船上的老水手们吵吵嚷嚷地忙着换班,不卸货就没啥好干的,冬天冷,水手长也没心思派工作。水手们整日无所事事,我乐得躲在房间里看书。
十几天后,公司命令我们转天津新港,靠码头开始卸货后,听老水手们说:这次接班的船长是第一次任船长,公司本命令我们下航次跑欧洲,可船长不想去,就对公司说:船上的船舶吊坏了,过苏伊士运河时无法吊装带缆工人的小船。
跑欧洲,老水手们当然愿意,航线长,时间久,拿的外汇补贴也多,靠港的国家也多,一个来回航次跑下来四个月就过去了。很多人就可以满载而归回家休假了。可这些没我啥事,因为我想在这条船上结束实习期,那就得干一年,对我来说下一航次去那都一样。
过了几天。公司海监室主任上船了。海监室是专管航行安全的。主任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也是我们海运学院的老毕业生,他一来就组织我们检查船况。经过一系列检查,他认定船上的船舶吊是坏了。其实在他来之前,水手长带我们检查过船舶吊。具我看那船吊怕是一两年没保养了,当然不能用了。可水手长也不叫我们修,大概是有啥想法吧。
于是公司令我们改去加拿大的罗伯特太子港装小麦。这一下全船上下更傻眼了。罗伯特太子港?那个港口的地理位置与我国最北边的漠河差不多,去那儿得走北太空洋高纬度!冬季的北太平洋风大浪高,可公司又明令本航次按美国气导航线航行。
“气导”全称是“气象导航。”以前,海员们从一地航向另一地,都是根据海图上的习惯航线,在分析当时的气候情况,天气状况,洋流分布,本船情况后,计划一条比较安全,经济的航线。到七十年代,美国人搞了一家气象导航公司,集合了一批资深船长,气象学家,海洋专家,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运用电脑建立了数学模型。将一船的启航港,目的港,船舶情况,货物种类等各种资料属入此模型。用电脑进行处理,得出一条最佳的航线,推荐给船长指导船泊航行。这是一种新的航海模式,一种新的航海概念,十年的应用证明:美国人推荐的这种模式使航线航程大大缩短,航程短程航行时间就短,航行成本就低,船货运周转量增加,经济效益好。当然船公司愿意按气导航线走。可船员们就不见得愿意。就拿从中国至加拿大西岸航线来说,过去的习惯冬季航线是走低纬度。从中国出发,自日本大隅海峡穿过,从夏威夷以北经过,到达美洲西岸。这样走风小浪低不辛苦,但时间要25天以上。按“气导”走,就要出日本北海道,穿过白令海峡,经乌尼马克岛到美洲西岸。航程只要20天。但白令海此时低压海洋水温低,气象复杂,低压气旋一个接一个,那就是说整个海区风力总在八级以上,海浪十分汹涌。
这两年凡是跑过此航线的海员们无不叫苦连天。听说有一条船去年过此海区时,风浪大得连驾驶台都没入水中,很长时间才冒上来。有多长时间?有的说三分钟,有的说五分钟,我想在那时候一条货轮成了潜艇,一秒钟人们都会觉的像一小时那么长。据说那艘船上的人们当时个个穿好礼服,还发了一封电报:祖国!再见了。电报传到公司,把领导们吓的够呛。
但公司命令不可违,航行任务必须完成,再说还有海监室主任在船上督导,尽管我们的船舶领导一再拖延,我们还是在1983年1月1日从秦皇岛出发向北航向加拿大。
冬天就是冬天,大自然按她的规律***,我们刚出航,船就在6,7级的风浪中前进,晃啊!摇啊!一天24小时没一刻安静。 出了北海道,船进入北太平洋,海上的风浪就更大了,风力达到8级以上,我们六个新毕业大学生大都不行了,晕船,呕吐,轮机部的小王更是吐的爬都爬不起来了,好在我天生就是航海命,一点也不晕,还吃的更多,你想呀,24小时每分钟都在动,体力消耗自然更大。
据医学上解释:在人头的后下部有一对平衡神经,它主控人的身体平恒,如果此神经较敏感,时间一长,就会疲劳失常,导致人呕吐,恶心。唯一的办法就是练,练的它迟钝了就不晕了。但晕船呕吐时必需吃食物喝水,补充吐出来的,不然吐完了食物吐胆汁,最后就***。只有吐了吃,吃了吐,几经锻炼,就不会再晕了。
我熬了一锅稀稀的绿豆粥,加上咸菜,逼着晕船的同学吃。他们强压着吃俩口,一转眼又喷出去。没办法,吐了还得吃,晕得最厉害的是轮机部的小王,他被我们绑在椅子上,面前的桌上放着粥,桌下是水桶。喝点粥就低头吐,吐完了漱漱口再喝,如此反复。
“不吃啦!打死我也不吃了,”他撕心裂肺的喊着。
“不吃不行呀,你总得过这一关,不然你还能在船上干么?”
水手长过来了:“哼!不吃就永远晕船,上了几年大学连这点风浪都抗不住,真是松包,这会外面风浪小点啦,你们俩不晕的,拖他上后甲板溜溜,吹吹海风,啥都好了。”
过了几天,其它的几个人还真不晕了,就小王还是不行,不管他晕不晕,二管轮还是命令他下机舱值班,可怜的小王一手提个小水桶,一手扶着拦杆,三步一口五步一吐,在机器的轰鸣中,油味中,一圈圈的巡视机器,一分一秒的值班,四个小时后,当他值完自己的班交班回到舱房时,他脸似黄蜡,浑身颤抖,趴在桌上口中喃喃的说道:
“我不活了,你们把我扔到海里去吧!”
当然,谁也不会扔他下海,他也就是在房间里说说,当着众人,他还是一付若无其事的样,是呀,我们谁也不想叫老水手们笑话是我们是松包。
折腾了十几天美洲海岸终于遥遥在望,风浪也小了些,晕船的这几个也都挺过来了。说来也怪,经过这次折腾,以后晕船他们再没晕过船,几年后我再次和和小王同船时,他已是二管轮了,航行时船外风浪再大,船再摇,他照样工作,打***,没事人一样。
白令海,北纬纬度45度以上,北极南下的冷流,冷空气,西伯利亚的高压冷气团,北美大陆的低压纷纷在这里交汇,这地方本来就不是人类生存之地。在卫星气像云图上,此地一个挨一个的低压气旋密密麻麻的挤满整个海区上空。一个移走了,另一个又移来了,有的干脆原地不动。等压圈间距不到三十海里,这就是说,此处风力总在10级以上,同时还伴有厚厚的云层和雨雪, 在我国,每到台风季节,人们把抗台风当做抗灾斗争,都认为台风是世界上最大的气象灾害,其实在还上十级风根本不算啥,就说白令海的这个季节,低压气旋的催毁力度一点不比台风差,台风还是过去了就没事了,可在此时整个海区低压气旋,高压气旋密布,除非你驶出这个海区,不然别指望风能停浪能小。
在船上很多地方都挂着倾斜仪,这倾斜仪是测船体平衡的,如果船是平的,她就指向零度。而我们走进白令海后,它就像个不倒翁,摆来摆去,最大的一天晚上,它突破了她的刻度最大值。。。。。38度。
这天上午我站在驾驶台,看着海水一遍遍的刷洗着门窗的玻璃,这驾驶台是全船最高的房间,平时它离水面有30米高,它下面有五层建筑。而此时海水直扑船楼,海水一遍遍的冲向船楼,船的前部像一根缝衣针,在海浪中穿上穿下。有时200米长的船除上层建筑外全部深深的埋入水中,过一会她又顽强的冒出海面。我趴在窗前向上望,天空就像是罩上了一口黑锅,灰黑色的云挤来拥去,只有被风吹成白雾状的海水,雨水在飞扬,海面上,已不能用浪花来形容,只能说是满满的全是白色的泡沫。
“涌“是形容海水中比浪更大海水波动,但这是什么样的波动呀,当浪打来时船只是晃一晃或上下颠簸,而一个涌涌来时,船体或是倾斜,或是摇摆,再不就高高的升上天空又狠狠的落向水下。如果浪涌是迎面而来,那船就会在原地不动,发出阵阵颤抖,抖的万匹主机顶不住,抖的人心阵阵发慌。
有一天,我们的船顶着浪涌整整顶了一天,到傍晚一测船位,我们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几海哩。
此时我目光向下看我们的船,老天!我的眼是不是看错了?将近二百米长,三万多吨的钢铁巨轮好像面条一样在扭?
“船长,我是不是看花眼了?”我满腹狐疑的问船长。
“你没错,去!到你住的那一层听听。”船长若无其事的说。
我跑到水手生活区的前壁贴在墙上听着,这地方的墙外边就是主甲板,
嘎吱!嘎吱!嘎吧吧!!
几十公分厚的钢板在痛苦的***。
格格格格!
半米厚的龙骨在叫。我们的船在扭动,甲板上,手臂粗的拦杆被浪打的弯曲扭斜,断了好几节。
老美的气导这时也不再发指导了,只是不断的把相关的气象资料发给我们,最后的一句话是:愿上帝保佑你们!
看来他们也只有指望我们天从人愿。
一天下午,雷达出故障了,二副判断是天线的电缆断了,没有雷达我们就成了瞎子,必须修好,但桅杆是全船的最高处,平时没风浪时爬上去都要小心谨慎。在此时别无选择,只有修复!
二副和一个老水手穿好雨衣雨靴,头戴安全帽,身上扎上安全带,他们勇敢的拉开门冲了出去。
船长,主任很不放心,也穿上雨衣走到驾驶台外面看他们爬大桅。狂风暴雨吹得船长,主任站立不稳,他们只好双手紧紧的抓住栏杆,用保险绳把自己栓在栏杆上,二副和老水手一点一点的爬上桅杆,此时桅杆的摆幅有十几米,他们用保险绳把自己紧紧得绑在桅杆上,在呼啸的大风中任凭雨水从头浇下,仔细的查找故障。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都为他们捏着一把汗,还好,不一会二副就做了一个“试试”的手势。下面的人一开机!雷达工作正常了。
二副和老水手小心翼翼的爬下来。带着一身的风雨,他们进了驾驶台,二副长长的松了口气,对船长说:
“接头松了!还好不是电线断了!”
可他俩的脸已被吹的发青,浮肿。
风浪最大的那天晚上,我值0-4班,半夜时分我上到驾驶台,此时的驾驶台人满为患,只见船长,主任,政委,轮机长,报务员,总之,船上的头头脑脑都在,人们一声不出,但我在微弱的海图灯光中看到他们的脸色铁青,凝重,汗流直下,有的人明显在发抖,我感到了气氛如此沉重。
这些老海员都是经过大风浪见过世面的,海龄都在十年以上,连他们都恐惧了,看来今天真是是够呛。
我也知道,下面各房间里人们也睡不着。人们全都用皮带把自己绑在床上,免的翻来倒去。
生?死?也许就在一瞬间发生,如果一声巨响。。。。。。。。
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会有人来救我们么?那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海况,这样的狂风巨浪,几百公里内飞机根本不能飞低,大船也无能为力。如果我今晚在此下去了?那也也够冤的。我才24岁!大学刚毕业,美好的海员生涯才开头。
上学时我们雄心万丈,就幻想有一天,身穿船长制服,袖口四道金杠,开着远洋巨轮飘洋过海,踏五大洋的浪花,走遍世界,历尽各国风光。
而眼下我们只有挺下去,闯出白令海!
不管闯得出去闯不出去,现在都不能松包!创出去了我们爱咋说咋说,创不出去我们也不能软!
想开了就不那么恐惧了。我全神贯注的摇着舵轮。平时无风时,这舵放到自动操作上,它会自动将船保持在预订的航向上,就是有点风浪,人工操做,也就是左右十度就够了,可现在这风浪需要我们不停的左满舵右满舵,把半个篮球场面积的尾舵操作的像一条不停摆动的鱼尾,这样才能勉强保持航向,我的带班水手晕船了,他一手抱着舵柱,一手尽力帮我摆舵,其实这会儿我并不觉的累,我叉开双腿,一边灵活的随着船的摇摆左右摇舵,一边心里不断乞求着:明海啊!你要坚持住呀!只要你不停机,不出故障,我们就一定能闯过去!人们建造了你,你就是我们生存的依靠啊!!!
四个疲惫不堪的小时过去了,到了交班的时间,我看到接班的水手也个个脸色苍白,知道他们没睡,晕船晕得也不行了,就主动提出我多值几十分钟。几年后,提起这事,已经官至交通部救捞局长的主任还记忆犹新,一碰到我就对众人说:
“哈!那关口,能站着说话的就是好样的,何况这家伙还多站了几十分钟!”
我们的明海轮还真是争气,我们来回近四十天的航行,她顶着风浪一点故障没出,满载34000吨小麦从加拿大回到了上海港。
开舱卸货,随着卸货抓斗的挖深,货仓中的货物里一个个圆柱型水湿货出现了,当货卸到一半时,大舱内的货物状况就像广西的石林一样,湿货柱大大小小,造型各异,圆柱林立。那是舱盖露下的海水浸泡了的小麦结成了结实的柱子。
港方的卸货指导员找大副问:“怎么会有这没多的货损?”
大副没好气的说“有多少?按海运保险合同规定,超过千分这四的货损船方才要赔偿。就是赔也是保险公司赔,船长一到港就向港监局递交了”海事声明“。海运法规定:凡船在海上遭遇七级以上风浪,船长只要到港后在规定的时间内递交了海事声明就可以免责。我们这次航行四十多天就没几天不是七级以上风浪的。而且我们也按海远法要求”尽责照顾了!”
指导员无奈,只好指挥吊车司机用抓斗将湿了的小麦打碎,掺和到好的小麦中卸下去了,只有已经发霉变黑的实在无法食用的,大约有两百多吨单独卸到码头上。
这些被水浸的货当然是损失了,可我们不是没采取措施,在罗伯特太子港装完货开航时,想到那因年久而锈烂的大舱舱盖根本不水密,水手长带着我们准备了大量的用油漆泡过了棉纱,堵满了舱口,等舱盖落下后,这些棉纱堵住了舱口不严的缝隙,我们又用布将一处处锈烂的小眼用油漆贴上,贴了好几层。可就算采取了措施,船太老了,她锈蚀遍布,一遇风浪有些没锈穿的地方也被扭开了,加上大风浪时舱面长时间的泡在水里,不出水浸货才怪。
卸完货后,我们对船上的损坏进行了修补。打断的栏杆焊上了,裂开的口子补上了。船厂的修理工们百思不解:是什么造成的这种损坏?
是海浪!
他们瞪大了眼,摇摇头,一脸的迷惑不解。
操作:oasis
[/bonus]请登录后发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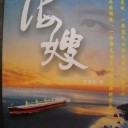
 联系我们人工客服
联系我们人工客服



















 :1391995811
:1391995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