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和朋友出去宵夜回家后无法进入梦乡吃饱了在床上撑着想起我父亲的,这对于我来说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因为我曾经读过许许多多有名的无名的、老先生新先生、男学者女学者写的怀念他(她)们父亲的文章,看了总觉得他(她)们的父亲是太伟大、太光荣、太不平凡了。然而他(她)们都说,他(她)们的父亲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父亲中的一个最普通的人,即便仙逝、光荣、驾鹤而去(以示对他的尊重)升到天堂里也是最普通的一员。而我那翘辫子后至今不知在地狱何处下油锅(我父亲说的)的老父亲呢?连普通的一员都谈不上。他原来有一个尊称叫贝先生、贝老师,被人罢了改称为贼。成了***的对象。那时我还小,不知道贼是什么意思。后来学会查看字典又经过我反复琢磨后才知道。贼在字典上有几种解释:一是做大坏事的人,如***贼;二是邪的、狡猾的、不正经(派)的,如他很贼;三是偷东西的人,如盗贼。我猜想他和偷东西有关。我这么认为的理由是:首先,他手中没有一点点权就连基本的选举权都被罢免了,不可能***,也卖不了国。其次,除了他狡猾地娶了我母亲被我母亲骂不正经外,左邻右舍的人都知道他很诚实。第三点,也是重要的一点,苟主任在批斗会上说的,他的长相贼头贼脑、贼眉鼠眼,一看就知道是个偷东西的人。
我父亲名叫贝少戎。能提出这么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来,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三里镇的人见了我父亲都称他贝二爷。贝家大爷呢?不在了。他是在我爷爷出征后的第三天“牺牲”的。据三里镇算命先生说,是被我父亲给克死的,道不同不相谋。
我父亲的名字是我爷爷提的。我爷爷和我**痛苦地分离后,便带着几个卫兵走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我**对我父亲说。我爷爷官大到能指挥近千号人,我想,可能是个校官吧!我父亲说,如果不被一颗流弹打中的话,现在肯定是个将官。还说,我爷爷光荣的时辰和我**生他的时辰是在同一个时辰,只不过差四天而矣。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生下我的父亲,并差人报到打过来打过去所谓的前线时,我爷爷和我**一样下身流满了血迹,所不同的就是出血的数量不同脸上的表情不同吧了。在他戎马生涯的最后时刻,我爷爷用手指蘸着他自己的血,使出浑身的劲,在地上行云流水般写下了“贝少戎”这三个大字。是让他儿子少一点兵戎相见?是让他儿子少年学成后投笔从戎任个元戎?还是含有其他什么意思?我们都无法去考证。据回报的家人说,我爷爷写下这三个字后,长笑一声,便抛下我可怜的、秀气的**先走了。我父亲后来猜测说,这长笑大概是向敌人说,我们贝家又生了个带把的能传种接代的人了,贝家是斩不尽、杀不绝的!
贝字是屋子底下一个人,命中注定贝家只能是单传。三里镇有名的测字先生对贝家前前后后发生的事作了以上说明。这和我爷爷的长笑,我父亲的猜测是差不多的。不知是巧合还是真的是命中早有安排,贝家没有断后,我父亲竟然伴着药罐子歪七扭八的长大了。当一个非常漂亮——能从我三个姐姐楚楚动人的脸蛋中就可以看出她年轻时有九成姿色的女人,创进了我那弱不禁风的父亲的眼睑后,我父亲说,他就开始茶饭不思睡眠不香像得了梦游症似的在邻镇宁家大院外转悠,再也听不进教书先生讲解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也是满心满肺满嘴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此,宁家大院里看门的母狗晚上就再也没有好好休息过。更为可怜的是如此忠于职守的它却遭到后来被我亲切地称为外公的那个人狠狠的一拐杖和它永远都听不懂的人话,让你贱!是什么不要脸的骚狗让你如此高兴的狂叫不止。我外公他哪里知道?在院外神出鬼没游荡的不是不要脸的骚狗,也是有头有脸、乐其不倦的我父亲——贝二爷。半年后,我父亲在花前月下用了一招巧妙的战术便得到了当时比我们贝氏家族还兴旺的宁氏家族二小姐的芳心。多美的夜晚噢!在一个有月光的晚上我父亲对我说。说完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激动地望着天上的月亮感叹道,小狗子(我**给我提的乳名说贱好养活),知道吗?月亮才是当今世界上最绝妙的、最行之有效的***剂!几年后我从记忆中才发现,我父亲他从不在有月亮的晚上出去做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事,就这事我问过我父亲。我父亲说,宁愿饿死也不去破坏心中那块美好的夜景。我知道我父亲的腿上有一块发亮的伤疤,是在宁家大院里被看门的母狗报复他时留下的。望着我父亲手舞足蹈的样子,冷不防回敬了他二句,我学着我父亲的语气对他说,多美的夜晚噢!狗尾巴花在尽情地摇来摇去。天上一个月亮噢!腿上一个月亮!我不知道哪个更光?哪个更亮?我父亲见我揭他的老底、泼他的冷水,望了望伤疤,不乐地骂了一句他常骂的话,狗东西!他那没头没脑的话语,让谁都分不清、闹不明他是骂我,还是在骂我外公家的狗。
我不由的大笑起来……
我母亲是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被贝家人用八抬大花轿抬回去给我父亲冲喜的。未过门时人们都叫她宁家二小姐,我父亲娶她过门后人们就改口称她为贝家二**。宁家二小姐是药引子,我**逢人便说,你看,贝二爷好多了。是的,真的是你母亲治好了我的病。我父亲肯定地对我说。我说,相思病?我父亲开心地说,不知道,反正好了。小狗子,你知道吗?你母亲过门那天把镇西边住的人都给吓得跑光了,我父亲又把我带到他浪漫的年轻时代。我说,为什么?我父亲说,放鞭炮。他们以为是枪炮声,土匪杀进村来了,能不快跑?
贝、宁连姻是个好意头啊!好就好在贝字和宁字合起来是个贮存的贮字(贮字繁写体是个贝字和宁字)。贝二爷,您要大发了!这是测字先生在我父亲和我母亲相好大办酒席的桌上连吃几块肉后,在乡邻们面前对我父亲说的。但旺财不旺丁。测字先生他没敢说出口,把话咽了回去,怕我那一家之主的小脚**一脚把他给踢出去,再也吃不到刚端上桌已半年没尝过鲜的红烧鱼。酒过三巡,嘴上有油关不住,还是说漏了出去。
果然,贝家的人丁不旺,家业却相当旺。这让测字先生高高兴兴赚了好几年的钱。可惜好景不长!贝家二**就让他像瘪了气的球一样,好久也蹦达不起来。贝家二**也就是我的母亲她并没有像测字先生他所测算的那样,是贝二爷春天采回来的一朵公花,中看不中用。在她那肚子平平坦坦好无动静的几年后,我们兄妹六个像花果山的猴子出入水帘洞般在她肚子里接二连三地钻了出来。事实证明,贝家二**是相当能生的,而且是越生越会生越生越有出息,先四个丫头片子后二个长把的小子。
这怎么可能呢?相书上说……测字先生猛摇他那不长毛的脑袋。相书放在手边,口水挂在嘴边,***坐在门边,连说三个不可能。他那三拳打不出闷屁的老婆没好气的接过话茬开口便骂,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少管贝二爷家的事。贝家得罪你了吗?为这事把本来就一只眼睛睁不开、一只眼睛闭不上的测字先生气得脑袋发蒙,身子发抖,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差点喘不过气连命都陪上。
活该!早就想踢他一脚去了。算他走运!没踢他自己倒爬下了。我**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这还真得要感谢我**这位开明女士当初没有把宁家二小姐赶出贝家的大门。为什么?曾有人问。我**说,宁家老爷她惹不起。我认了!从我父亲一言一行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我**讲的话是真的。
这一点我相信!
提到我父亲,就会讲到我母亲,必然也就牵涉到我。我是在我**把我母亲养得膘肥体壮再努力努力生他一个带把的让测字先生心服口服的号召下,从我母亲的肚子里舒舒服服呆了九个月后顺利钻出来的。出生后,曾被人们称为贝二爷家的贝二少爷,但大多数是在我甜滋滋地啜着我母亲***的时候他们捏着我肉嘟嘟的白里透红的脸蛋时说的,而且后面必加一句,好吃吗?我母亲总是抬头一笑大声说,好吃。香着呢!然后望一眼我们贝家对面不远处的测字先生家,看看那位坐在门槛上曾四下谣言我母亲不会下蛋的测字先生有什么反映。
别以为你宝贝!他们是冲着你母亲丰满的***也不是冲着你丰满的***,我父亲拍打着我的***干瞪着他的眼睛指桑骂槐地说道。他心里清楚他不敢惹她、骂她,更不敢打她、休她,只能找她的儿子出出气。只可惜我太小!未能听懂我父亲和我母亲打情骂俏般的争吵。我父亲最后肯定在我母亲那娇滴滴滑溜溜令人流口水的叫骂声中败下阵来。这些是我父亲在送我外出读书的路上告诉我的。最后还特别强调一句,不要和女人一般见识,把自己的威信丢了。我说,算了吧!我母亲不在了死无对证。唉!我父亲听了就重重的叹一口气不再言语。
我母亲是在我一岁的时候,丢下我们去做“地下工作者”的。我父亲说,你母亲是死于不应该死的一个故事中,和你**一前一后上的黄泉路。没有大米饭吃?死后还背着了个黑锅干什么?去做饭?黄泉路那边有好多好多米是不是?小时候饿得慌,想亲娘总是这么追根究底问我的父亲。问急了我父亲就张开嘴巴,愤怒的瞪着双眼朝我吼,狗东西!这才使我搞清楚、闹明白他为什么在不开心时总要骂一句狗东西。原来是骂我们三里镇革命委员会最高行政长官苟主任那个苟(狗)东西。在你一岁那年,苟(狗)东西苟(狗)眼看人低想亲你母亲,亲不成反被你母亲重重的咬了一口。我父亲沮丧着脸说。
新闻!新闻!人咬苟(狗),真是天大的新闻!一传十,十传百。测字先生像只被吹胀了气的球又活跃了起来。他那添油加醋的讲解,推波助澜的演说,在小镇上引起轩然大波。不难想像,这怎能不让曾经在贝家看过门护过院的苟主任丢尽脸面,怀恨在心。她们想变天?没门!大权在握的苟主任轻轻松松说了一句。同样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他不动一枪一炮又轻轻松松的把我母亲和我父亲的母亲前后一起送上了黄泉路。从此炼就了我父亲一双发光的眼睛。我父亲那烙痛我心多年的眼光曾使我后来琢磨过,他为什么晚上出去不用灯?难怪!简直就是二眼愤怒的火山口。
请登录后发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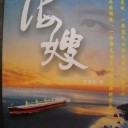

 联系我们人工客服
联系我们人工客服



















 :1391995811
:1391995811

